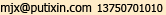|
弃舍渴爱,精进于苦行
心中自然想起三个从未听闻过的譬喻。
譬如有一块浸在水里湿润、多汁的生木,有人拿着一个上面的取火木钻走来,心想:“我想生火,我想取暖。”你认为如何?此人是否会用木钻去磨擦那块浸水而湿润、多汁的生木,生火并取暖呢?”──“不会的,世尊!为什么呢?因为那块生木本身既湿润又多汁,且它又浸在水里。所以那个人只会徒劳与失望。”同样地,当一个沙门或婆罗门身心都尚未远离感官的欲望,当他尚未弃舍乃至平息对感官欲望的贪欲、喜好、热爱、渴求与痴迷,那么,不论这善良的沙门或婆罗门,是否经历痛苦的、折磨的与刺穿的感受,在任何一个情况下,他都不能获得智、见与无上正觉。这是我从未听闻过,第一个在心中自然生起的譬喻。
然后,譬如有一块离于水置于干地的湿润、多汁的生木,有人拿着一个上面的取火木钻走来,心想:“我想生火,我想取暖。”你认为如何?此人是否会用木钻,去磨擦那块离于水面而置于干地的湿润、多汁的生木,生火并取暖呢?──“不会的,世尊!为什么呢?因为那块生木虽已在干地上,远离水面,但它本身仍是湿润、多汁的。所以,那个人只会徒劳与失望。”──同样地,当一个沙门或婆罗门身心都尚未远离感官的欲望,当他尚未弃舍乃至平息对感官欲望的贪欲、喜好、热爱、渴求与痴迷,那么,不论这善良的沙门或婆罗门,是否经历痛苦的、折磨的与刺穿的感受,在任何一个情况下,他都不能获得智、见与无上正觉。这是我从未听闻过,第二个在心中自然生起的譬喻。
然后,再次假设有一块离于水面而置于干地的干燥枯木,有人拿着一个上面的取火木钻走来,心想:“我想生火,我想取暖。”你认为如何?此人是否会用木钻,去磨擦那块离于水而置于干地的干燥枯木,生火并取暖呢?”──“会的,世尊!为什么呢?因为那是块干燥的枯木,且又离于水而置于干地上。”──同样地,当一个沙门或婆罗门身心都尚未远离感官的欲望,当他尚未弃舍乃至平息对感官欲望的贪欲、喜好、热爱、渴求与痴迷,那么,不论这善良的沙门或婆罗门,是否经历痛苦的、折磨的与刺穿的感受,在任何一个情况下,他都不能获得智、见与无上正觉。这是我从未听闻过,第三个在心中自然生起的譬喻。
我又想:“假如我咬紧牙根,舌头顶住上颚,以自己的心去打击、箝制、压迫自己的心,那会如何呢?”然后,犹如强壮者抓着弱小者的头与肩膀,打击、箝制、压迫他,我咬紧牙根,舌头顶住上颚,以自己的心去打击、箝制、压迫自己的心。当如此做时,汗水从我的腋下流了下来。
虽然我生起不疲厌的精进,也建立起不断的正念,然而身体变得劳动过度且不平静,因为这痛苦的精进让我感到精疲力尽。不过,如此痛苦的感受对我的心完全没有影响。
我又想:“假如我修习止息禅,那会如何呢?”我于是停止用口、鼻吸呼。当如此做时,我听到很大的风声由耳而出,有如铁匠鼓动风箱时所发出的吵声一般。
我停止用口、鼻与耳朵吸呼。当如此做时,强风撕绞着我的头,我的头仿佛被一个壮汉用利剑劈开。然后便是剧烈的头痛,仿佛有个壮汉正使劲地勒紧箍在我头上的皮条。接着,强风割开我的腹部,仿佛一个熟练的屠夫或其学徒用利刀切开公牛的肚子。之后,我感到剧烈灼人的腹痛,仿佛有两个壮汉抓住一个疲弱的人的两个胳膊,把他放在一堆煤火上烧烤。
虽然我生起不疲厌的精进,也建立起不断的正念,然而身体变得劳动过度且不平静,因为这痛苦的精进让我感到精疲力尽。不过,如此痛苦的感受对我的心完全没有影响。
那时,当诸天见到我,他们会说:“沙门乔达摩死了。”其他天人会说:“沙门乔达摩既未死,也不在死亡边缘;沙门乔达摩是个阿罗汉、圣人,因为圣人之道就是如此。”
我又想:“假如我绝食,那会如何呢?”不久,诸天来到我这里并说:“善男子!别完全绝食,若你如此做的话,我们将把天人的食物注入你的毛孔,让它维持你的生命。”我想:“既然我宣称要彻底绝食,而这些诸天却把天人的食物注入我的毛孔,让它维持我的生命,那么我就打妄语了。”我说:“没有必要。”于是便遣走了他们。
我又想:“假如我吃很少的食物,例如每次只喝少量的豆子汁、扁豆汁或豌豆汁,那会如何呢?”于是我便这样做了。当如此做时,我的身体变得骨瘦如柴,四肢变得像接合在一起的藤条或竹节,只因为我吃得太少。我的臀部变得像骆驼的蹄;隆起的脊椎骨,犹如串起的珠子;肋骨瘦削突出,犹如旧谷仓屋杂乱无章的椽木;眼光深陷入眼窝,犹如深井中映现的水光;头皮皱缩,犹如因风吹日晒而皱缩凋萎的绿葫芦。若触摸肚皮,就能摸到脊柱;触摸脊柱,就能摸到肚皮。大小便时,头会向前倒去。当以手搓揉四肢以放松身体时,身上的毛发因根部烂坏而纷纷脱落,只因为我吃得太少。
当人们看到我时,他们会说:“沙门乔达摩是黑皮肤的人。”其他人说:“沙门乔达摩不是黑皮肤,而是棕色皮肤的人。”更有别的人说:“沙门乔达摩既非黑皮肤,也不是棕色皮肤,而是白皮肤的人。”由于我吃得太少,清净、皎洁的肤色因而损坏了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