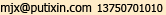| 第十一章 佛陀其人
(续)
跋耆长者巧驳外道
阿难:一时,佛在瞻波城伽伽湖畔。那时,跋耆长者于一日午时出瞻波城去见世尊。但路上他心想:“此时不宜去见世尊,他应正独处静默;此时也不宜去见禅修的诸比丘,他们正独处静默。我何不先去外道游方沙门所住的园林?”
他去到了那里,其时外道游方沙门正在集会,谈论种种低俗的话题,人声鼎沸。看到跋耆长者从远处而来,他们提醒彼此安静,说道:“诸大德!不要作声,安静莫语。跋耆长者将要到来,他是沙门乔达摩的信徒,瞻波城中,倘若尚有白衣,是沙门乔达摩之徒,此人必是其中之一。此等贵人,不喜噪音,谨慎小声,称赞小声。如见我等寂静不语,他或便生亲近之念。”
游方沙门于是沉默下来,跋耆长者来到后,向他们寒暄问候,然后坐于一旁。他们问道:“长者!看来沙门乔达摩反对苦行,一向严厉诃斥责备每个修苦行而导致艰苦生活的人。这事属实吗?”
“不是的,大德!世尊诃责当诃责者,称赞当称赞者,他必定是分别论者,而非一向论者。”
一位游方沙门对他说:“且慢,长者!你所称扬的沙门乔达摩,依据你所言,他是对任何事物都无设定的虚无论者。”
“与之相反,大德!我当以理对诸大德说,世尊确实有设定何事为善,何事为不善。因此,世尊确实有所设定,并非无设定者。”
如是说后,诸游方沙门随即沉默。
人之痴与不痴
注释者:一位信仰尼乾陀①的人,他的一个儿子萨遮迦来到毗舍离与佛陀辩论。佛陀提到自己觉悟前的精进,如何使他发现苦行不是证道之途。他说:
阿难:我曾向数百听众说法,其中或有人想:“沙门乔达摩在为我一人说法。”但他不应如此认为,因如来是为令大众知之而说法。当说法毕,我即摄心于内,使它平静,使心专一、专注在我说法之前的相同所缘上。”
“沙门乔达摩是应供、等正觉者,此事自是可预料的。但沙门乔达摩可曾在白天睡眠呢?”
“在热季的最后一个月,食后由乞食归来,曾将大衣褶成四迭,右胁而卧,正念,正知而入眠。”
“有些沙门、婆罗门,称此为痴人之住。”
“人之痴与不痴,不决于此。人若未舍断那些垢染、重生、未来之苦、导致生、老、死的诸漏,我说他即是痴者,因为他尚未舍断诸漏,所以他是愚痴的。若舍断诸漏,我说他即是不痴者。因为他舍断诸漏,所以他是不痴的。譬如多罗树,截其顶冠,便无再生之机。同样地,如来已舍断、切断、根除诸漏,如截断的多罗树头,归于无有,于未来已无再生起之法。”
世尊如此说时,萨遮迦观察说:“真是稀有啊!乔达摩大师,真是不可思议啊!当乔达摩大师一再受到别人对他的人身攻击时,他的肤色愈加光亮,面色愈加清澈,正如应供、等正觉者。我曾有幸与富兰那迦叶辩论,他在这种时刻支吾其词,转变话题,甚至显露愤怒、瞋恨与粗暴。我又与末伽梨瞿舍利,以及许多人有过类似的经验。那么,乔达摩大师!在此告辞了,我们很忙,还有许多事待办。”
注释者:但萨遮迦并未被说服,而仍保留原来的观点。
阿难尊者代佛陀说法
叙述者:有一个事件说明佛陀也不能免于疾病。
阿难:一时,世尊在释迦族迦毗罗卫城外之尼拘律树园。那时,世尊病愈未久。释迦族人摩诃男前来世尊处,说道:“世尊!我久知世尊所教之法:‘得定者有智,不得定者则否。’世尊!是先定而后智呢?还是先智而后定呢?”
阿难尊者此时思惟:“世尊病愈未久,这位释迦族人摩诃男却向他请教一个艰深的问题。我何不把他领到一旁,为他说法呢?”
于是,他就这样做了,他说:“世尊说有学者的戒,定,慧,又说无学者的戒,定,慧。所谓有学者的戒,是比丘为具戒者,以别解脱律仪防护,圆满正行与行处,见微细的罪过也感怖畏,以受持学处而学。所谓有学者的定,是比丘入于并住于四种禅其中一禅之中。所谓有学者的慧,是比丘如实了知:‘此是苦,此是苦集,此是苦灭,此是灭苦之道。’至于所谓圣弟子者,具足戒、定、慧,他依漏尽、无漏,于现法自证知,住于无漏之心解脱,慧解脱。”
译注:
①尼乾陀是印度古代六师外道之一,此外道主张修苦行,离世间之衣食束缚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