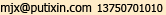|
方法
“若有人欲得蛇,见一大蛇,不得其法,误执蛇身或蛇尾,蛇返身咬之,他因此而受死或受将死之苦。何以故?因他捕蛇不得法故。同样地,有迷途者学法,不以慧究明其意义,也不喜于静思其义,反以之作为挑剔别人与反驳批评的工具,不明学法之目的,以误取其义故,反造成长久的伤害与痛苦。但若人欲得蛇,见一大蛇,以叉具擒之,执蛇之颈,蛇虽可以身缠蜷其手臂或四肢,他既不会受死,也不受将死之苦。同样地,某族人学法,以慧究明其意义,也喜好静思其义,不以之为挑剔别人与反驳批评的工具,深明学法之目的,以明了其义故,而致得长久的利益与安乐。”
“诸比丘!若有旅人见大水流,此岸危险且恐怖,彼岸安全而无恐怖,但无船、无桥可渡。思索之后,他捡拾草枝、树干、树枝、树叶,系成一筏,浮在其上,手脚并用,努力划动,终得安度彼岸,达彼岸后,他想:‘此筏甚为有用,助我得度;我何不将它顶在头上或负于肩上,随我而行?’如此,他对此筏所做得当否?”
“不然,世尊!”——“他当如何做呢?若在得渡后,他想:‘此筏甚为有用,以其助我得度故,我何不将它托至干地,或任其飘流,以便我可随意而行?’如此,他对此筏便作了得当的处理。如此,我示汝之法正如筏,为得度故,非为执取。诸比丘!当你明白筏喻,便知(乃至善)法尚应舍离,更何况恶法。”
目的
“贪、嗔、痴的止息,是无为、究竟、无漏、真谛、彼岸、微妙、极难见、不衰、永住、不分解、不可见、寂静、不死、无上、安泰、安稳、爱尽、不思议、稀有、无灾、无灾法、涅槃、无损(不害)、离欲、清净、解脱、非住、岛屿、庇护所、港湾、皈依处、彼岸。”
第十三章 提婆达多
引言
前文虽提到过佛陀与僧团遭人误解、诬陷的故事,其险恶的程度却远远不能与本章的情节相比。更有甚者,策划杀害佛陀的阴谋并非外人,而是其堂弟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本是佛陀的弟子,但当其心为名利攫取后,从请佛退位开始,发展到三次图害佛命,以及分裂僧团的不赦之行,就迅速地走上罪恶之路。
本章中也介绍阿阇世王子在受到提婆达多的迷惑后,就犯下行刺父王,遣派杀手,欲杀害佛陀等一系列的恶行。在登上王位之后,他又无端地挑起战火,与波斯匿王两次以大军相对,而终于沦为阶下囚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,他的父王以德报怨,在刺杀他的阴谋被揭穿之后,不但不惩罚祸首,反而将王位让出;以及波斯匿王不忘亲情,在俘虏了阿阇世王后,又将之释放的义举。
本章中包含不少后来广为流传的佛经故事。例如提婆达多推石欲杀害佛陀;佛陀慑服野象;舍利弗与目犍连劝服五百比丘回归僧团,只是其中的数例。对于提婆达多堕入地狱一节,此处虽有提及,但也说明其根据非源于巴利三藏。
我们还可看到,提婆达多曾对佛陀提出五点苦行的要求,遭到佛陀出于中道立场的断然拒绝。三净肉的规定,便是此时佛陀针对提婆达多不吃鱼肉的请求提出的。我们不妨在此顺便指出,根据巴利三藏经典,佛陀从未倡议不吃鱼肉的斋食。
注释者:提婆达多是佛陀的第一个堂弟,他篡夺佛陀之位的图谋据说发生在佛陀成道之后的第三十七年,亦即佛陀七十二岁时。
叙述者:下面是律藏中对此事的记述。
迷惑阿阇世,获得利养
优婆离:那时,提婆达多独处静默时,心中思惟:“我从何人嬴取信心,因而能获得利养、荣誉与名声?”他于是想到:“当是阿阇世王子处。他年轻,前途光明。我何不嬴取他的信心?诸多利养、荣誉与名声都可由此而生”
如此,提婆达多收拾卧具,持钵与大衣,动身前往王舍城,终于抵达该处。到达之后,他弃其本形而化身作一青年,众蛇缠腰,并以此装束出现在阿阇世王子的膝上。阿阇世王子感到怖畏、焦虑、疑惧、忧虑。提婆达多于是问到:“王子!你可对我有所畏惧?”
“是的,我很畏惧。你是何人?”
“我是提婆达多。”
“尊者!你若是提婆达多,请现出本形。”
提婆达多于是弃舍青年之身,立在阿阇世王子面前,着大衣,手持衣与钵。王子由于提婆达多的神通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心。此后,他日夜以五百车乘、五百份乳粥供养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被利养、荣誉与名声所蔽,野心盘据其心,生如此的欲望:“我将统领比丘众。”但随着这一念头的生起,他的神通就立即消失了。
世尊在乔赏弥随意地住一上段时间后,便次第游行,前往王舍城,并如期到达,住在迦兰陀竹林园。那时,一些比丘来见,禀报世尊:“世尊!阿阇世王子每日早晚亲自以五百车乘与五百份乳粥供养提婆达多。”
“诸比丘!别羡慕提婆达多所获的利养、荣誉与名声。如同将恶狗鼻下的囊包刺破,只会使这恶狗变得更暴恶,只要阿阇世王子如现在般供养提婆达多,提婆达多的善业就会不断地消失而不是增长。如同芭蕉树结实后便导致自己的毁灭与衰败,提婆达多所获的利养、荣誉与名声,将导致他自己的毁灭与衰败。” |